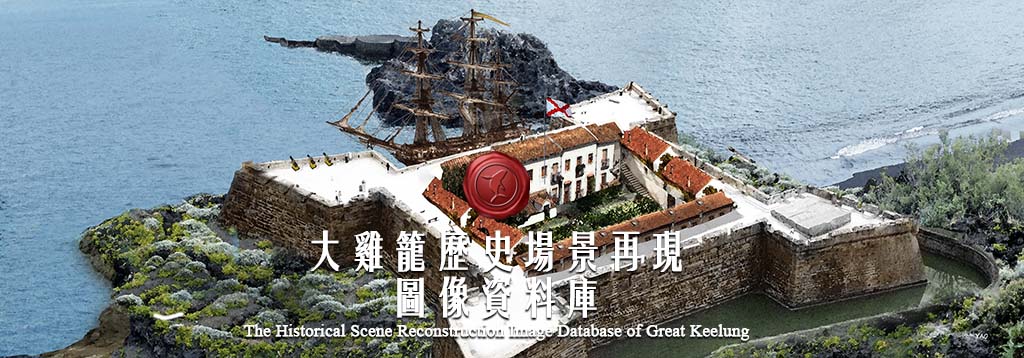|
|
|
明朝的態度
明朝對雞籠的態度,可以張燮在《東西洋考》裡的敘述為代表:「雞籠雖未稱國,自門外要地。」(註1) 亦即雖非版圖,但因位置重要,必須重視。 明代自1549年開始海禁到1683年解除,在此期間非正式的貿易方式造成倭寇的興起。1553年海盜王直(汪直)率200艘船進犯江浙,與俞大猷及戚繼光在1553年發生普陀山之戰及1555年發生台州之戰,王直敗退,部份倭寇逃往台灣,使得台灣成為海盜的聚集地。1557年葡萄牙獲得澳門為據點,同時協助明朝控制了倭寇的行動,這讓明朝在1568年部份解除禁令,開月港(海澄縣)為私人貿易的口岸,同時其他西方商人包括西班牙與荷蘭人也在此時開始現身。(註2) 在這樣的環境下1570年雞籠與淡水成為明朝官方認可的貿易地點,1590年規定每年可以有10艘船到雞籠與淡水交易,但事實上當地的土產品並不足以支撐10艘船所需的貨物量,這些中國船極有可能是來此與來往呂宋之間的日本商船進行交易。(註3)在這種以台灣為境外交易中心的狀況下,讓鄭芝龍的閩南海商集團應運而起。 我們應注意一點,明朝指定雞籠與淡水為官方認可的貿易地點並不表示朝廷認為那是國內,正好相反那兒被認為是國外,因為明朝管的只是中國船隻的數量與它們被允許去的地點,至於有多少艘日本船或西方船去台灣交易是管不著的,因為那兒不被認為是明朝的疆域。有一個著名的例子可以證明1622年荷蘭艦隊第五次攻打澳門失利,移師占領澎湖在風櫃建立城堡,當時明軍逼迫荷蘭人拆毀城堡離開,華商李旦建議荷人轉移到大員(今台南安平),因為那兒是明朝疆界之外。這件事情表示在朝廷眼中澎湖與台灣是不同的身份地位。(註4)
雖然雞籠不是明朝的疆域,但中國官員卻徵漢人到此漁商的船引稅,甚至更早有出巡馬尼拉漢人村落的事件。由於中國傳統是「天下」的觀念,與其他國家是「朝貢外交」的非平等關係,所以我們很難用近代歐洲「民族國家」(Nation state) 的概念來解釋。以下舉幾個真實的例子: 他們逗留在馬尼拉的期間穿著官服乘轎在前呼後擁下招搖過市,沿途華人跪拜,甚至在澗內開庭審理司法業務,引起西班牙高等法院的不快,更引起總督的猜忌,以為中國人要來攻打,這些人是先遣部隊,於是開始對華人社區監視防範,雙方的不信任造成數個月後的大規模屠殺事件。(註6) 在事件中有25,000名華人被殺,剩下的200名倖存者全都被送上槳帆船當搖櫓手,其中有一個原來在馬尼拉就是頭人的富商名叫李旦。1606年6月由於中國政府的過問,這些華人在日本被釋放,李旦落腳平戶,從此開啟了海商兼海盜的傳奇。(註7) 李旦是說服荷蘭人放棄澎湖佔領大員的關鍵性人物,他為這件事派出的通譯聯絡官就是鄭芝龍,鄭芝龍在李旦死後承接了他的船隊與地盤,創造閩南海商集團勢力的高峰,這些也是鄭成功征台的發家資本。 其次是關於宦官高寀,他會來呂宋考察金山,是因為他「礦稅監」的身份。明代因朝鮮戰爭財政入不敷出,萬曆皇帝派遣親信宦官到各地名義上是開採銀礦及在各交易要衝徵收商業稅,但實際上這些宦官都集中在大都市,並不是因為都市產銀,而是他可以任意指定富豪之家說房子地下有銀礦要拆毀人家房屋,屋主只好送上大筆賄賂以保住家園,宦官甚至率領一批無賴搶劫商民形同盜匪。其中派在臨清的宦官馬堂就因為欺壓太過在1599年引發當地民變,被弭平後馬堂依然穩坐原位,次年6月馬堂又搶劫了路過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帶往北京晉見皇帝的珍稀獻禮,利瑪竇向北京友人訴苦,友人卻回覆要他「捨財保命,因為如今皇上只聽宦官之言」。(註8)
礦稅監宦官劫掠地方不僅是中飽私囊,事實上整個事件都是因為要應付萬曆皇帝的奢華開銷而起,包括修建定陵龐大工程的開支。這場宦官引發的掠奪史稱「礦稅之禍」,(註9) 高寀的福建礦稅監就是因此產生的職務,所以會跑到馬尼拉勘查金山也可算是「礦稅監」的業務範圍。在明代福建方志「閩書」(註10) 中可以查到更多關於高寀的記載:
關於這件事在「閩書」的另一卷關於袁一驥的敘述可以看到更多記載: 對於明代太監的跋扈,閩書可說寫得十分傳神,不過在書中卻找不到海澄縣令王時和與百戶干一成的資料,但這份出訪馬尼拉的名單是根據明史323卷的記載,應有可信度。(文中的「嶷」就是甲米地金山案的始作俑者張嶷): 而迫於朝命,乃遣海澄丞王時和、百戶幹一成偕嶷往勘。呂宋人聞之大駭…..(註13) 金山的謊言終於破滅,王時和回福建不久羞憤而死,始作俑者張嶷被干一成向朝廷告發,最後被刑部以「張嶷等無端欺誑朝廷、生釁海外,以致二萬商民盡遭屠戮;損威遺禍,死有餘辜。」罪名斬首示眾。(註14) 1627年又有一批中國官員來到已被西班牙人佔領的雞籠,記載提到有部份之前曾去過馬尼拉,但根據閩書高寀在萬曆42年(1614年)被撤職回京,所以在1627年派員來雞籠的就不太可能是高寀,而王時和已在1617年去世,也不可能來雞籠。來者可能是一位千總或把總,到剛被西班牙人佔領的雞籠一探虛實 。(註15) 這批中國官員來雞籠,主要是因為荷蘭人曾賄絡中國人向官員進讒言說西班牙人是壞人,不要跟他們合作,因此前來「看西班牙人是怎樣的鄰居?」這些官員受到西班牙人很好的接待。由於當時西班牙人已經佔領雞籠一年多,中國官員此時才來應該不是為了雞籠的事。當時中國與荷蘭因拆遷澎湖堡壘的事尚處於敵對狀態,就已經有中國人在替荷蘭遊說了,整體來說是福建不同的利益團體為了競爭商業貿易的利益,分別派出遊說團企圖影響中國官方的決策。(註16) 從中國官員來到已被西班牙人佔領的雞籠這件事可知,顯然明朝官員根本不把西班牙的統治權放在眼裡,認為華人即使到了海外還是大明王朝的子民。 清代大部份時間朝廷是重南輕北的,雞籠被視為邊陲的蠻荒之地,連地方官都沒有,直到1874年沈葆楨來台視察,發現雞籠因採煤業興盛,他在報告中寫到:「洋樓客棧,闤闠喧囂…..通商之後竟成都會,且煤物方興,末技之民四集,海防既重,訟事尤煩,該處向未設官,役非佐雜微員所能鎮壓」因此奏請設雞籠通判,並將「雞籠」改名「基隆」,取「基地昌隆」之意 。(註17) 隨著基隆開港,輪船時代來臨,有深水港又有煤炭礦產優勢的基隆馬上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