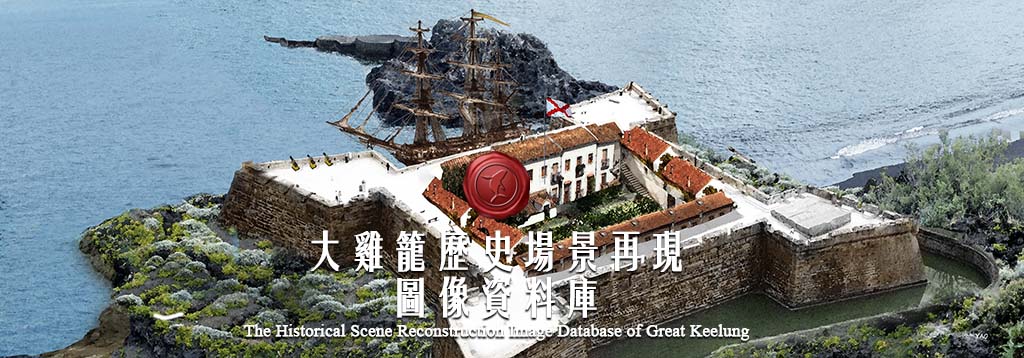|
|
|
雞籠的日本人聚落
《明史‧外國傳》中曾有記載: 嘉靖末,倭寇擾閩;大將戚繼光敗之,倭遁居於此,其黨林道乾從之。已道乾懼為倭所並、又懼官軍追擊,揚帆直抵浡泥,攘其邊地以居;號道乾港。而雞籠遭倭焚掠,國遂殘破。始,其人悉居海濱;既遭倭難,稍稍避居山後。忽中國漁舟從魍港飄至,遂往來通販以為常。至萬曆末,紅毛番泊舟於此,因事耕鑿,設闤闠,稱台灣焉。(註1)
可知嘉靖至萬曆年間日本倭寇就已經來此劫掠原住民濱海的土地並曾遁居於此,這批倭寇後來為明軍所逐,之後又有日本商人前來採金,所以1626年西班牙人登上和平島時,發現島上竟已有中國人與日本人的市集。(註2)
根據岩生成一著〈在台灣的日本人〉論文中,認為日本人在台灣北部相對於台灣南部來的較少,因為朱印船貿易的重心是荷蘭人的熱蘭遮城,來雞籠的只有1631年與1632年(即寬永八、九年)共5艘而已。(註3)
岩生成一在文中提到荷蘭指揮官雷爾生(Cornelis Reyersen)在他的航海日誌中曾記載關於日本人對雞籠的印象: (註4)
「再據日本人說,基隆Kelang灣雖有充分水深足以讓大船進港,但當地居民幾難以信賴,對我們或許不利。」(註5)
不過岩生成一僅根據朱印船的數量認為日本人在北臺灣人口較少,卻沒有考慮其他移民因素,譬如幕府對西方宗教迫害時日本天主教徒來雞籠避難的可能。當時日本人往東南亞移民呂宋最多時達到三千名,暹羅亦有一千五百名,主要是走投無路的浪人、天主教徒、貿易商人以及受雇於當地人或外國人的日本人。(註6) 所以日本天主教徒會來到雞籠應非特例。如當時在雞籠最著名的日本人喜左衛門,他是京都人,1603年因船難來到雞籠,娶當地Kimaurij原住民女子Insiel Islena為妻,有兩個女兒與一個早逝的兒子。喜左衛門是天主教徒,教名Jasinto Quesaymon,諳葡萄牙語,西班牙人來到雞籠時雇用他做為通譯與嚮導,並為他的兩個女兒舉行盛大的洗禮做為宣傳。喜左衛門甚至到1643年之後以63歲高齡仍然繼續為荷蘭人服務。(註7)
那麼日本人在雞籠的聚落位於何處?傳教士Esquivel Jacinto神父說:「聖薩爾瓦多是主要的港口,我們同樣也有兩件工作,一是在中國生理人的Parián執行教務,另一個是建立醫院照顧生理人、當地住民與日本人。(註8)」
楊彥傑在《荷據時代台灣史》中曾敘述:「大河灣附近設立街市,稱澗內,吸引中國人和日本人前去居住。」此處「大河灣」應為「大沙灣」之誤。 (註9)
還有一段敘述:「因為越來越多中國人說想在肥沃低地開墾和種植甘蔗,他們甚至說,今年他們將逐漸給日本工人額外的土地,不用付租。 (註10)
在翁佳音著《大臺北古地圖考釋》中曾敘述:「該堂原址之上,後來是否有可能再建修道院,暫難得其詳。另外,Esquivel Jacinto神父曾建議教會當局在金包里村社中的慈濟院(La Misericordia)旁邊,替漢人、原住民與日本人建立一間醫院。據此,似乎可推測圖上的兩間修道院中,有一間應為「慈濟院」。 (註11)
根據各資料對教堂、醫院與生理人、日本人、原住民的敘述應為同一個地方,或有可能在社寮島對岸的大沙灣或八尺門水道岸邊。
|